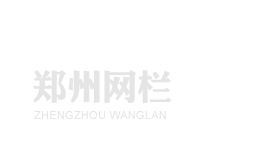再谈李鸿章-----赵一飞
来源:欧宝直播APP 发布时间:2025-09-08 18:16:13当我的学生在前史课上对李鸿章全盘否定,将其简略标签化为“卖国贼”“奸细”时,我觉得很有必要谈一谈客观的点评前史人物的必要性了,这远比给出一个非黑即白的结论更为重要。
我在开学榜首课上曾说过,我国古代史总能让每个我国人心生骄傲。前秦诸子激荡出“百家争鸣、百家争鸣”的思维巅峰,汉朝喊出“犯我强汉者,虽远必诛”的雄壮气势。南朝祖冲之将圆周率准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,抢先国际近千年,而整个南朝(宋齐梁陈)也只是连续169年,假如一个人能活100年,那也得起死回生的阅历10次。隋唐更不用说,与亚欧非各国的广泛往来铸就盛世盛名,“唐人”的称谓自此传遍四方。宋元时期,海交际易的昌盛远超前代,海上丝绸之路弯曲穿越百余国,活字印刷术、指南针、火药相继传入东亚、东南亚与欧洲,深入改写了国际格式与人类文明进程。即使到了开端落后于国际的明朝,也仍有“皇帝守国门、君王死社稷”的时令与郑和下西洋的豪举值得铭记。
反观我国近代史,却满是压抑与憋屈。尤其是战役之后,清朝控制岌岌可危却又百足不僵,致使这个陈旧的东方大国一步步走向衰败,大众饱尝涂炭之苦,生灵有倒悬之危。从道光皇帝开端,后续君主更是一代不如一代。道光朝查处林则徐,签下《南京公约》《虎门公约》等一系列不平等公约,敞开了羞耻的近代交际;继承者咸丰帝以“仁孝”之名继位,却在英法联军攻陷北京、火烧圆明园时避走承德避暑山庄,临终前的权利组织更将王朝面向慈禧太后擅权的深渊;同治帝或许曾有励精图治之心,虽造就时间短的“同治中兴”,究竟不过是王朝的回光返照,后期耽于放纵,19岁便英年早逝;若说同治帝是“傀儡皇帝”,那光绪帝就是彻里彻外的“提线木偶”。用我的话来说,这哥俩肯定算得上一对难兄难弟,在慈禧老佛爷的掌控之下都没得到一个好下场。
现在,我要说的是李鸿章,当然我也不宠爱这一个晚清官场上的“老油子”。现在史学界对他的点评也是贬多褒少,单单其建议抛弃新疆一事,足以担负一世臭名,更不提在其为官任上“宰相合肥全国瘦”了。但公私分明,若仅凭这些便将“卖国贼”“奸细”的帽子扣在他头上,不免有失公允。
纵观李鸿章的终身,生于官宦世家,1847年中进士,后升任为翰林院编修,尔后在晚清的浊世中逐渐兴起。他曾参加平定太平天国运动、捻军,为维系清王朝控制立下丰功伟绩。19世纪60—70年代洋务运动中他更是中心实践者,先后兴办军事工业江南制作总局、金陵机器制作局、天津机器制作局等,为我国军工奠定根底。编练新式陆军(淮军),换装西式兵器(收购英国“李-恩菲尔德”步枪、法国“米涅”步枪、德国克虏伯火炮),延聘英法教官推广西式练习,树立近代戎行编制。
筹建北洋水师时,他一手推进建筑威海卫、旅顺等水兵基地,订货英国“超勇”“扬威”等巡洋舰,向德国购买“定远”“镇远”“济远”等主力舰,声称“亚洲榜首、国际第九”,但是甲午海战一役,北洋水师全军覆没。他也曾打着“求富”的旗帜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和近代书院,如轮船招商局、开平矿务局、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,企图以实业支撑国家开展。
在人才培养上,李鸿章相同颇有远见。1872 年,李鸿章与曾国藩奏请“遴派幼童赴美留学”,至1875年,清政府共遴派4批120名幼童赴美,这中心还包含詹天佑(我国铁路之父)、唐绍仪(民国榜首任总理)等后来的近代化主干,后又兴办天津水师书院、武备书院,为我国近代水兵与陆军培养了榜首批专业人才。
由此可见,这位饱尝争议的晚清官员,在国家危亡之际仍是做了一些事,不论他是出于保护清王朝的控制或许自己的声誉的意图,至少不是在潜身缩首,苟图衣食。这不由让人联想到当下的网络怪象,总有一些做实事的人被诬蔑为博眼球、沽名钓誉,而不干事的喷子却能站在品德的制高点敲得键盘啪啪作响。
当然,前史的功过可不能相提并论,更不能功过相抵。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要交际官员,代表清廷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公约,严峻损害了我国的疆域主权、经济利益和国家庄严。我梳理了一下大约如下:中日《北京台事专条》(1874年)和《中英烟台公约》(1876年)共赔款70万两白银;《中法新约》(1885年)补偿法国200万两白银;中日《马关公约》(1895年)补偿日军军费2亿两(后因 “三国干与还辽”,清政府额定付出“赎辽费”3000万两,总计2.3亿两);八国联军侵华签定《辛丑公约》(1901年)补偿各国军费白银4.5亿两,分39年还清,本息算计约9.8亿两(史称“庚子赔款”),以海关税、盐税作典当,将我国拖入更深的财务深渊。
清朝向各国赔款数额之巨,纵观人类前史也是罕有的,而李鸿章作为这些公约的参加者和签署者,要说这些羞耻跟他一点联系没有,也没人服气。当然,让人愤慨的,绝不止赔款这么简略,疆域、司法、关税自主权损失,我国的事不再由我国人说了算,打碎牙只能往肚子里咽,这才是最可悲的。
无妨再回忆 1895 年马关商洽时的一个细节。3 月 24 日下午,日本外滨町的路旁边挤满了围观人群,都想亲眼目击这位大清钦差大臣的容貌。前一日,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向他提出极端严苛的休战条件:占据大沽、天津、山海关,接收津榆铁路,清政府承当休战期间日军军费。李鸿章发电请示清廷后,当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。
在他回来住宿地的途中,一个叫小山六之助的青年从路旁边的人群中蹿出,左手按住轿子,右手掏出手枪,从李的右侧向其面部开了一枪。“挂彩的李鸿章当即以右手的长袖掩住创伤,毫无震动的神色,情绪泰然处之。目击这一幕的我感叹,真不愧是了不得的人物”。(引自下関郷土会編:《郷土》第11集,1965年,第89页)
万幸子弹不大,又或是李鸿章的确命大,他的伤势并不严峻,十几天后创伤已渐愈合。但由于其年事已高,不宜开刀,总算这颗子弹就此一向留在他的血肉中直到盖棺,或许,这也是命运对他终身功过的某种隐喻。
在后来的商洽中,日方赞同将赔款从3亿两白银削减到2亿两,而这1亿两的退让并不在日方原先的预案中。有人说“李鸿章挨了一枪,给大清省了一亿两”,这也不无道理。
可细想之下,这是他能为那个行将倾覆的帝国大厦能做的一切了。这一刻,你能要求一个72岁的白叟还做什么呢?他去或不去商洽早已情不自禁。或许退一万步来讲,总不能让慈禧太后亲赴敌营交涉吧。我想,那一刻的李鸿章,心中定是充满了力不从心的疲乏与苍凉。换做现代人60岁退休,72岁早已儿孙绕膝、安享晚年了,愈加不用说去替国家和民族担负臭名了。
假使前史有假定,李鸿章能生在当下,依据他的生平缓洋务运动期间的体现,我觉得他应该会成为一个军事家或许交际家,亦或许教育家也不无或许。在强壮祖国的支撑下,或许面临战役他不用让北洋水师困守威海卫港,在跟外国交涉时也能够挺起胸膛,宣布最强音“你们没有资历说站在实力的视点跟我国商洽”, ——而这一切的底气,都源于国家的强盛。
李鸿章是清朝衰亡史的书写者,但他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,有功,亦有过,乃至过大于功。但咱们仍需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他,究竟,他与那个迂腐的清王朝相同,都没方法真实独当一面地掌控自己的命运,更无法反转一个年代的沉沦。